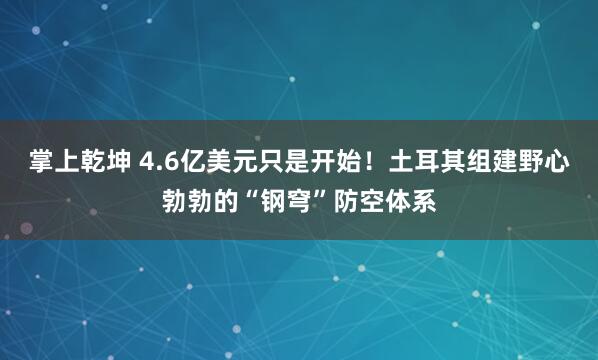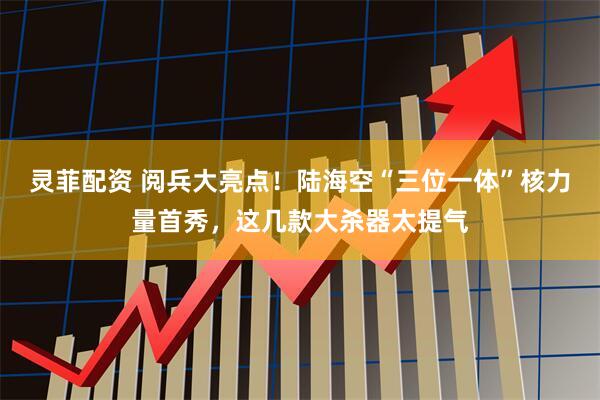1934年10月10日,中共中央率2个纵队,从瑞金岀发,开始走上长征路涌融优配,与此同时,准备参加战略转移的所有红军主力,除红9军团因任务特殊,集结在会昌业珠兰埠外,其他全部集结到了于都河北岸。
根据中央事前制定的转移方案,主力红军及中央所部,被编成左、中、右三路。其中,左路由红1军团、红9军团组成,中路由中央及所属机关编成的2个纵队组成,右路由红3军团、红8军团组成,整个后卫则由红5军团负责。如下图所示:
在国家军事博物馆,收藏着一份极珍贵史料,名为《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廿日行动日程表》,逐日明确了所有参加长征部队的日行军或作战计划,在当时是高度机密。根据不久后朱德发布的命令,此计划自12日开始,所有日程向后缓延一天。
展开剩余89%当中央2个纵队到达指定位置后,所有已集结在于都县境内的主力红军,于10月16日晚,分10余个渡口,同时开始南渡于都河,也走上了长征路。
根据中央的绝密计划,所有参加战略转移的单位和个人,必然在21日前抵达赣县、信丰、安远三县的结合部待命,当然也划定了所有单位的集结地点。
为什么要全部集结于此?因为在蒋介石发动第五次“围剿”以来,敌人已在中央苏区的四面八方,构筑了密如铁桶般的封锁线。中央红军要顺利实行战略转移,就得撕开敌人的封锁线,杀出一条血路,才能跳岀外线。
中央启动战略转移的初衷,本计划转到湘西与红2军团、红6军团会师。所以如何突破,在哪里突破,均根据这一战略目标制定,当然也要考虑敌情和统战等原因。
中央在紧锣密鼓酿酿转移方案期间,已派何长工、潘汉年秘密出访国军粤系首领陈济棠,经过艰苦谈判,与“南天王”陈济棠达成5点共识,正式签暑了包括“借道”在内的秘密协议。于是中央将突破敌人封锁线的突破口,选择在了陈济堂所谓粤军负责的防线。
从实情而言,由粤军负责的这道防线,北起赣县,南至安运,以天堑桃江为核心,以王母渡为转折点,总体呈西北至东南走向。以河流、山谷、碉堡、壕沟、铁丝网为载体,构筑起南北约120公里,东西宽约50公里的立体交织防线(下图中的黑色线路,即代表封锁线)。
结合多方面情况,中革军委将突破口选择在了江西信丰县的韩坊,至安远县龙布镇之间的封锁线上,其中间点就是后来因首战而闻名的信丰县新田镇百石村。
既然己明确选定韩坊至龙布间为突破口,那所有机关和人员当然要提前集结在此封锁线之前,一旦前锋部队打开了缺口,即可鱼贯而出。
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前,所定的集结区域,就在今江西省赣县、信丰、安远等三县结合部。如上图中密集的红色箭头所示区域。
以2个中央纵队为例,就是从下图中所谓的祁绿山红军小道,穿越弯弯曲曲的山间道路,到达百石村东北侧一带的集结区域,其中红军总部的指挥所,就设在那个名为“合头”的地方。百石村所在位置,就是长征第一仗打响的地点,史称“百石战斗”。时任红3军团第4师师长洪超,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个红军师长,就是牺牲在这里。当地政府已在此规划建设长征第一仗核心展示园,也为洪超烈士建有陵园、纪念碑、展示馆等。
发生在百石村的长征第一仗,于10月21日上午10时打响,虽然这是一场早已谋划好,且必须打的仗,但仍然存在突发性。总部原确定的总攻击时间为20日晚至21日晨,但由于有部队未到达指定区域,故总部将全线总攻击时间推迟到了21日晚至22日晨。
红军把突破封锁线的总攻击时间,向后推迟了一天,但战场形势往往波橘云轨,当红4师的前锋部队抵达百石村,开始侦察前行时,突然遭到敌人设在百石村境内的前沿阵地的袭击,红军被迫还击,长征第一仗就此暴发。
经过一番激烈战斗,红军虽然付出了阵亡师长的惨重代价,但还是较顺利地毙伤敌军无数,夺取了阵地,残敌被迫逃窜。
就在红3军团第4师打响百石战斗,并取得胜利的同时,中央纵队的所有单位和个人,已全部到达赣县、信丰、安远三县结合部的指定区域。此外,担任左、右两路侧翼安全的红8军团、红9军团,也推进到了各自的最佳位置。此时,距中央纵队正式出发只有11天,距主力部队南渡于都河也仅5天。这里其实就是赤白交界地,稍不注意,险情随时可能发生。
由于不了解实情,又无专业书籍可供查考,有许多人在谈论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时,总有一个错觉,认为其与第四道封锁线类似,就是一条自然天堑桃江。其实这是误解,桃江只是封锁线其中的一段,北起赣州,南至信丰县的王母渡,敌人的确充分利用了桃江这一天然沟壑,但到了王母渡以南地区,敌人的封锁线已越过桃江,前出于韩坊→百石→新田→龙布一线的崇山岭林之间,开始呈现西北→东南走向。敌人之所以如此设立,大有学问,也大有用意。
第一道封锁线,主要由陈济棠所属粤军设立。所处位置就是上图中的黑线。粤军之所以这样构建封锁线,即要向蒋介石表决心、交差事,更要确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。其实,陈济棠的最终目的,并不是要歼灭红军,而是在于防止红军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。所以,只要红军不进入广东省境内发展,他们就睁一只眼闪一只眼。
也正是因为陈济棠与蒋介石貌离神合,所以中共中央能够在启动战略转移之前,派何长工、潘汉年出面,与陈济棠顺利达成所谓“借道”秘密协议。中央军委也就能够放心地把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突破口,选定在赣县、信丰、安远三县之间的结合部。
也许又有人提岀这样的疑问,中央不是已与陈济棠达成了秘密“借道”协议吗,为何还是有惨烈的战斗?为何还是要靠武力去征服?
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,关乎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,关乎党中央的生死存亡,关乎红军战士的生命安危。虽然的确已与粤军提前达成谅解,达成秘密协议,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和前途,押注在这纸基础并不牢固的协议上。因此,在正式开始战略转移前,红军决不可能把自己的战略意图和行动计划,提前透露给对手,以避免落入敌人伏击圈。
其实,即使是在红军内部,这样的绝密计划,也只有极少数最高层领导才知道。所以,中央红军要突破敌人的第一道防线,只能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和顽强的战斗意志,去强行借道。而作为陈济棠的粤军,为了洗脱暗通红军、不战而退的罪名,也绝不可能把已经与红军达到的绝密协议向下传达,也只能是局限在极少数的最高层掌握。所以,红军要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,只能是强行借道。只有在战斗真正打响后,再通过双方高层各自的调兵遣将和布局谋篇,自觉寻找达到某种默契和某些方面的妥协。
往事已过去近90年,又因“百石战斗”早已盛名在外,现在有许多人错误认为,红军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,仅打了“百石战斗”这一仗。其实这是一种错觉,根据总部的计划和命令,总攻于21日晚至22日晨全面打响。发出在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上的战斗,并非单点突破,而是呈现全线打响,多点攻击的态势。战斗主要集中在信丰县的韩坊镇、至安远县的龙布镇一线。
除了最先打响的“百石战斗”,比较有名气的还有“金鸡战斗”“新田战斗”“石背圩战斗”“古陂战斗”“安息战斗”“安西战斗”等。此外,在信丰县桃江河泮的王母渡,右路后卫红8军团还有那里打响了“王母渡战斗”。大大小小的战斗,共约10多起。而中央纵队在经过固营时,因为偶发事件,在行军途中又突然打响了“固营战斗”。
若论战斗的惨烈性,以“王母渡战斗”居首,因为敌人在那里设有最坚固的碉堡群;若以战斗规模的大小论,“古陂战斗”居首,因为这里是敌军的一个师部;若论战斗的突然性,以“固营战斗”居首,因为中央纵队在通过此地之前,已经通过统战关系达成了默契,但中央纵队大约通过一半时,防守此地的民团临时受人鼓动,突然凭借坚固的堡垒向外开枪,红军被迫还击。
按最理想的状态,中央红军全都到达预先集结区域后,前锋部队根据预定作战计划,多点同时发起总攻击,迅速抢占敌人阵地,全面撕破封锁线后,即紧急赶往桃江河边,紧急架设浮桥,为中央纵队渡河创造条件。从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看,也大都按照事先预定的计划在执行,并无太大出入。也就是说红军在突破敌人第一道防线期间,虽然中间时不时出现一些偶发因素,但总体上基本达到完美状态。
在回到战场,从实际发生的情况看,虽然红3军团的前锋红4师先遣部队,率先打响了“百石战斗”,但绝大部分的战斗,主要集中在21日晚至22日晨,多点开花,全线攻击,战果辉煌,全部达到预定目的。其实,所有战斗仅打了一天,加上提前打响的“百石战斗”,也只有接近2天时间。防守第一道封锁线的粤军余汉谋部,虽然像模像样抵挡了一下,但很快就开始执行秘密协议,命令粤军开始向南康、信丰、安远等县城集结。也就是说,粤军稍加抵抗,就为中央红军让开了中间的通道(如上图蓝色箭头所示)。
于是,红军总部命令前锋部队,立即翻山越岭,迅速赶往坪石、大塘埠、铁石口一带的桃江河边,这里就是中央红军,特别是2个中央纵队的预定渡河区域。
红军前锋部队一面分兵警戒四周敌情,一面组织力量开始紧急架设浮桥。23日至25日,各路红军依序渡河,到25日为止,包括担任后卫的红5军团在内,所有红军已经全部跨过桃江,进入到湘南、赣西南、粤南交界区域,又踏上了准备去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的道路。
从中央纵队于10月10日自瑞金出发,至10月25日全部渡过桃江,中央红军仅用了15天时间,就成功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,全部跳到了外线。
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的悲壮历程就此开始!红军万岁!涌融优配
发布于:天津市长宏网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